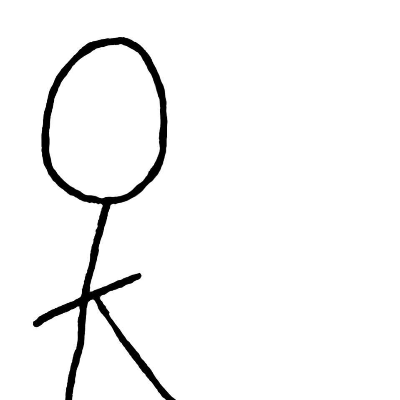章鱼p
我的理解是
章鱼噼的问题就在于
它的目的
人类世界发生的无论多么没有道德多么令人悲伤
它这波操作下来
👍
老是想着happy,结果呢
本来静可能会被茉莉乃霸凌致死
茉莉乃肯定脱不了干系,会受到法律制裁的
(就算没有这也是这个系统里本来发生的)
但章鱼噼以异于人类世界的存在出现
还顺手一魔法板砖把茉莉乃敲死了
它还不承担法律责任
换言之,它因为自己的叛逆,违反了它老家happy星的规矩
造成了1-5集悲剧
它要是不出现也一样是悲剧
但是它插手了
就像
治疗心理疾病
淳平看到一孩子心理有问题
于是自告奋勇来治愈
结果把人家治死了。
性质就从
自杀变成了被教唆自杀
然而这个淳平还不是淳平,是一个看着人畜无害,动机纯良的外星章鱼噼
章鱼p的存在对于这个都是非正常人的社会关系系统
某种程度上来看是残忍的
对于每个个体可能会因它而露出笑容
作者这么写也是挺狗的
看完我的感触就是
放下助人情结,尊重他人命运
[捂脸]
好吧
章鱼噼最后也是牺牲自己换来了一个ge
怪不得那时漫画完结观众不满呢
那些破事作为叙事主线
最后这么搞相当于他们所说的梦结局了(还是噩梦)
(果然最后一集的ed是后半段
😭😭)
还好
和解了
这样处理一想还挺好的
章鱼噼动用了规则之力
把感触经验留下来了
可以理解为
额
没有欲望主体的形态
只留下了爱
这很好。
也可以说,原生家庭的问题是无法改变而且深植于孩子心理的,章鱼噼结局带来的是后天的魔法之爱,这是种现实中很难带给他们的爱。谁也不知道这个故事后续会怎样发展,静香和茉莉乃他们确实成为了朋友,东君也渐正常了,但不知道章鱼p留下的这种魔法之爱到底多好使。
这帮梅姨阁诗人从小内心就扭曲,虽然有章鱼噼的魔法之爱(超现实的结构式爱),但长大后呢?是不是和前面章鱼噼的无能一样,对于那些主体结构,那些创伤无能为力?
虽然这么说很残忍,也很没有人文关怀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机构任何一个个体能够拯救他们,如果没有章鱼噼,就那么发展下去,就算惨也是那个糟糕的环境系统的必然。
精神分析说什么穿越幻象,可是在那个环境下,谁能“认识你自己”?谁能天天研究些抽象的精神分析理论?
如果像我这样持悲观态度看这个故事中的角色,那么作者这么写很温柔了,不是什么报仇不是什么正义的制裁,只是“正常”生活下去...
往好了说,至少活下去了,有那个“认识你自己”“穿越幻象”的可能性了
“教溺水者游泳”是理想的却很荒谬,章鱼噼可能是先“给溺水者救生圈”,虽然没有解决问题却能让人活下来
让我康康!